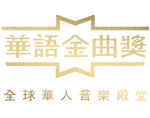《東莞時報》“鄧偉標自由創作
在喧囂與浮躁共舞、焦慮與消極共存的時代,一部分藝術家,往往與落魄、貧窮相伴,在癲狂與平庸的分界處,孤影自憐,晃蕩不安;還有一部分,在資本與權力面前,低眉順眼,婉轉溫柔,以求得生存的一方晦澀天地;剩下的,是拋棄藝術,揚長而去。
這一切,鄧偉標洞若觀火。“我認為,到今天,作為一個普通人,我非常成功,我的成功不是因為我賺了多少錢,不是因為我創作出了貝多芬那樣偉大的作品,我的成功是,我真正可以自由創作,並且在這個自由創作的過程中,能養家糊口。我覺得這已經是很高的境界了。”鄧偉標真誠地說,話語間,有柔韌的感恩。
鄧偉標屬於中國流行音樂明星制的第一代製作人。在那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時代,他滿懷激情與憧憬,興沖沖往前趕。幾年下來,成績斐然。但榮譽和掌聲湧起的時候,激情卻慢慢冷卻下來,理性則適時來到。
1996年,鄧偉標獲得了“中國流行音樂10年成就獎”,這個在外人眼裡看來光輝熠熠的獎,在鄧偉標的生命裡,卻成了他與流行音樂默然告別的標誌。原因是,他認為中國流行音樂只是跟在港臺後面,亦步亦趨,並沒有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來。
只有對音樂真誠追求的人,才能真正客觀地判斷自己音樂的價值。鄧偉標帶著一種失望和無奈,這樣評價自己的流行音樂創作:“其實就是一堆垃圾。”誰年少不輕狂,只是,當輕狂為理性讓路之時,正是精神趨於成熟的時候。
告別流行音樂後,鄧偉標開始了顛沛的闖蕩,做廣告公司,投資網路,最後以一敗塗地的狀態收場——員工都被炒光,自己則連吃飯的錢都沒有。靠網友的資助,鄧偉標艱難地度過了人生的低潮。
對音樂的真誠追求,則未曾離去。經歷了那種因為失望而絕望的沉鬱,他終於迎來因為絕望而重生的喜悅。困厄至極,重拾音樂,仿若新生。山窮水盡之時,恰雲起風生,《空》誕生在鄧偉標最貧困的時候,猶如一場豪奢的喜悅,自由的創作過程,給了他前所未有的體驗。
之後,他進入了的音樂創作的豐盛期,相繼出版個人音樂作品專輯《千江匯流》、《古城今昔》、《紅樓十二釵》、《瑩瑩花語》、《新世紀粵曲I》、《色》、《情殤》、《古情記》、《寒風鎮電影原聲大碟》等,作品廣受喜愛。
加拿大的《Glean》雜誌這樣評價鄧偉標:“他特立獨行堅持創作自己的音樂,如狂風暴雨中屹立的岩石,不合時宜卻又被越來越多的聽眾接受,成為一種無人敢複製又難以解釋的音樂現象。”
2008年,網友們發現北京奧運主題曲《我和你》,與鄧偉標《無覺》極為相似,認為是《我和你》的創作者陳其鋼,抄襲了鄧偉標的作品,亦有部分網友認為是鄧偉標抄襲了陳其鋼的作品。此事一時轟動了輿論界。
鄧偉標發表聲明,《無覺》創作時間為2005年,自己沒有抄襲陳其鋼。並表示,自己的聲明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而保護自己的尊嚴,並不意味著去傷害另一個人的尊嚴。當網友轉而傾向于認為陳其鋼抄襲了鄧偉標時,鄧偉標則表示,據樂譜技術分析,陳其鋼沒有抄襲自己的作品。
在輿論風暴大肆挺進之時,堅持良善的溫情,堅持客觀的理性,頗費心力,然而鄧偉標做到了,他收穫的是人們發自內心的敬意。訪談中,鄧偉標告訴記者,陳其鋼是他很敬重的音樂人,國內很多領域都出現了抄襲作假的現象,大家相互指責,戾氣很重。他不希望音樂界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同室操戈,有令人難以承受的悲涼。不如互相信任,互相鼓勵。
2009年,被稱為中國新世紀音樂領軍人物的鄧偉標,創建了中國首個新世紀音樂組合——五行元素樂團,他的音樂人生,步入另一個高點。深入傳統,堅持原創,五行元素樂團,等待著在時間的洗滌之後,沉澱出璀璨的結晶。
最近,那些瀕臨絕境的民俗音樂,成為了鄧偉標關注的焦點,“如果不及時搶救,它們就永遠消失了。”他準備製作一些音樂作品,用方言來吟唱。他以他的執著,以及對民間文化的敬意與溫情,行走在搶救民俗音樂的路上,成功與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動。
——對話
生命裡最不重要的事情是寫小說
《東莞時報》:國內有些媒體把鄧先生稱為中國新世紀音樂的代表人,你是怎麼評價新世紀音樂的?
鄧偉標:在我的創作理念裡,沒有門派風格的界定,我向來以比較自由的態度來看待音樂。傳統的音樂家習慣跟風格走,我的音樂,從2005年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定風格。
新世紀音樂不是一種風格,它是一個臨時的名稱,不是一種技術名稱。在世界上有了電子合成器後,開始出現一種完全與曾有的音樂都不同的音樂形態。
當你把音樂物化成一種商品來消費後,就不知道該怎樣定義它。新世紀音樂的本源可以追溯至幾乎所有現存的音樂流派,從古典到流行,從歌劇到電子,從民族到爵士。
新世紀音樂是一種統稱。它打破權威的約束,打破創作的定則,打破流派的藩籬,以不定之規,譜寫自由之音。雖然同在新世紀音樂的名下,藝術家們的作品,彼此風格卻是千差萬別。
總體上講,自由、包容、創新,是新世紀音樂的創作理念。
《東莞時報》:除了音樂創作外,你還曾寫過科幻小說?
鄧偉標:呵呵,是的。我總共寫了一百萬字左右,其實不多。我嘗試著把科幻的東西和古龍武俠的東西放在一起寫。我喜歡看科幻雜誌,喜歡那些神秘難解的事物。我之所以寫科幻小說,其實受科學雜誌影響。我的科幻故事,很多東西都是有科學依據的。寫小說與創作音樂都需要一種無厘頭的想像力。當然,我並不認為我的小說有多好看。寫小說,在我的生命裡,是最不重要的突發事件。
西施的故事,悲絕淒涼
《東莞時報》:你的作品《西施•情殤》,用波瀾壯闊的音樂,來刻寫細膩婉轉的古典愛情故事,很有驚豔之感,但是,有人批評你,西施的故事,特別是西施與範蠡的愛情故事,是野史,而非正史,認為你不夠尊重歷史。
鄧偉標:很多人把我這個故事看做是虛構的,不尊重歷史。其實歷史本來就存在虛構的東西,中國人下意識地會允許古人瞎編,卻不允許現代人瞎編。因為中國人歷來沒有機會看到真正的歷史,歷史都是由帝王書寫的。在沒有真相的時代裡,謠言成了不得不信任的信源,古人的敘事,則自然而然成了信史。
我用音樂寫過一些女子的悲慘的愛情故事,寫得最棒的,就是西施的故事。
在我的故事裡,西施是一個被男人利用,用到盡的工具,完全沒有被當做一個人。她成為間諜之前,只是一個浣紗的女子,吳國與她無關。但是,她就硬是被勸說過來,灌輸以家仇國恨,被硬生生地訓練為一個出色的工具,送至吳國。
她唯一的感情依託是範蠡,一往情深。她認為只要完成了殺吳王的任務,就可以和心愛的人相守至死。但其實不然。
西施被送至吳國後,吳王對她非常好,是真心的好,極致的好。世上很少有女人,能得到這樣真摯深切的愛。但是西施卻對此全然無知。她得到吳王的真心,然後殺死了他。西施沒有認識到自己和吳王的愛,才是真正的愛。
等到越國迎西施回國,越王看中了西施,範蠡無奈,只能拱手相讓。西施才感到自己原來無路可走,她選擇自殺,是一種極致的悲涼,沒有任何文學作品能表現。自己親手殺死了愛自己的人,自己愛的人卻把自己看做一個工具,甚至將自己轉讓給他人。
西施悲絕淒涼的故事,其實是幾千年來女人共同的命運底色。我一直覺得,女性,從古至今,都是較弱勢的群體,所謂的平等,其實從來沒有真實地發生過。
步入絕境,獲得極致的平靜
《東莞時報》:你原先是做流行音樂的,後來怎麼轉而進入新世紀音樂的創作?
鄧偉標:我是中國流行音樂明星制的第一代製作人,就是專職製作明星。上世紀90年代最初的時候。當時是充滿熱情地去做這些事情。到1996年的時候,開始慢慢有一些理性。
1996年,我獲得了中國流行音樂10年成就獎,我拿到那個獎的一瞬間,非常不開心。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流行音樂很爛,包括我自己,就是一堆垃圾,沒什麼可以慶祝的。
我們的流行音樂是跟在臺灣後面,不斷模仿,走不出自己的路。我回來後,就不再做流行音樂了。因為我覺得再做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了。
我選擇做廣告公司,投資網路,然後賠光了錢。到2004年,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一群網友,籌錢來支撐我的生活,讓我堅持下去。到最後,我真是走投無路了,想自己唯一能賺錢的,還是作曲。
在王文光老師的幫助下,我重新開始創作音樂,只是我不再做流行曲,而是來做純音樂。我當時到了一種山窮水盡的貧窮狀態,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反而擁有了一種極致的平靜。很平靜的時候,寫的音樂,的確不同。
當時創作的就是《空》,那時我內心平靜到可以晚上8點睡覺,早上4點起床,一個月不出門。我非常享受當時平靜自由的創作過程。
可以說,從《空》開始,我真正進入我的音樂人生,真正開始享受創造。
《東莞時報》:有人說,《空》之所以暢銷,在市場上獲得了極大成功,是因為《空》給人們一種寧和境界,安撫了都市人焦躁的心靈,你自己是怎麼看的?
鄧偉標:我覺得《空》的成功,主要是獨立,很高的原創性。我認為聽音樂,簡單說來就是消遣,就是生活某一瞬間的一個背景,沒有幾個人可以在聽音樂的時候,帶著一種哲學的研究態度。大家聽著我的音樂,感覺很舒服,那我就覺得很好了,甚至可以說功德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