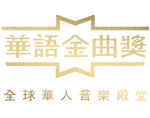華語音樂顛峰論壇(五)——馮翰銘:我想西方人瞭解中國詩詞的美
游:游威(華語金曲獎總策劃) 馮:馮翰銘(香港金牌製作人)
時間:2013年12月5日
地點:廣州中國大酒店
記錄/整理:柯曉婷

華語金曲獎總策劃游威與香港著名製作人馮翰銘
游:你好,Alex,這次跟你做的這個訪問是“華語音樂巔峰對話”系列之五,之前都是一些前輩好像呂方、周治平、李麗芬等,你其實是最年輕的一個了。近幾年香港的流行樂裏面像陳奕迅、容祖兒、何韻詩他們的作品全部都有你的名字。雖然未必每個歌迷都認識你,但只要說到你的作品,是無人不識的。所以我很好奇,當年你在國外讀爵士課程,算科班出身,但是回來又做回了流行樂,這其中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呢?
馮:其實挺有趣的,我記得我19歲那年去了美國波士頓讀音樂,那個學校在美國是被稱為“音樂軍校”的。我讀完回來之後並沒有朋友帶我入行,我靠的是一本黃頁。(游:哈哈,那麼有趣?)那時候正東唱片叫黃柏高的經紀人,我就問有沒有人認識他,因為我想自薦我的音樂給他聽。但是沒有人認識他,所以我就按照黃頁打電話給正東唱片說我想找Paco,他的秘書就問是誰找他,我說我叫Alex,有一些創作的作品可能Paco會喜歡,然後她就笑了半分鐘,因為應該每天都有不少這樣的人撞上去,我只是其中一個。但是我估計那個秘書姐姐心情很好,我又很好運氣,她就跟我說,好吧,你把你的履歷表和demo寄過來吧!隔了兩天,Paco就打給我了,說有沒有興趣上來公司見個面。(游:哈哈,好像神話那樣!)對,好像神話。進去了以後,我本來是簽給Paco做唱作歌手的,但是Paco說我的名氣還不是很大,要把我捧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旗下有很多歌手,有許志安,有蘇永康,不如你幫他們寫一些熱賣的作品,讓別人知道你的名字,然後我再推你出來這樣會更容易點。就這樣過了三年,他也沒怎麼推我,我也沒怎麼想他去推我,所以可能我們的關係就這樣完結了。然後我就和另一個拍檔陳奐仁(Han Jin),組成了一個音樂製作團隊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從陳冠希的“香港地”開始一起監製了很多唱片,像王菀之的《手望》、《畫意》等等。
游:那當時做製作和自己做歌手的心態應該不同吧?
馮:非常不同!因為當我要為其他歌手製作一張唱片時,主角一定是那個歌手,所以整張大碟的主題、概念和內容都是圍繞那個歌手的,作為監製就要在藝術和商業之間找到平衡,不能很自私,一味地做自己喜歡的東西,一定是要做適合那個歌手,能夠幫助那個歌手的作品,所以這就是我以前專注的部分。
游:對,其實我自己也覺得簡直是有兩種的,一種是為別人度身定做,根據歌手的風格去做合適他的作品,另一種就是很自我的,無論什麼歌手,總之做出來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個風格。但這也是其中一種風格,也有它好的地方。
馮:是啊,這樣可能會標新立異點,但是其實是一種很強烈的個人風格。我以前和陳奐仁建立“隱形人製作”的時候,也使用了類似的模式去運作,這樣別人一找“隱形人”就知道他們的風格是比較西化、重型節奏的,可能有Hip-pop、Rap,甚至中國風的作品。但是隨著年紀增長,我自己的體驗多了,反而變得客觀了。我覺得一個監製的責任不是去標新立異,更加不是捧紅自己,而是輔助你的歌手找到適合他的風格,找到自己的音樂,找到他的路,不然,我覺得就不是一個很稱職的監製。
游:我覺得李宗盛大哥就是這樣的,他真的能夠把每一個歌手的特點和優勢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但是你一定還是會感覺到大哥的那種味道!就是無論萬芳還是辛曉琪,你一聽就可以感覺到這是李宗盛做的,這就是他的標籤咯。至於Alex你的風格,我覺得是會有古典,又有現代,就是跨界的東西比較多。
馮:我想是因為我是比較注重多種音樂性的一位監製。也很有趣的是,很多和我合作的歌手本身就是挺有料的了,(游:哈哈是啊,都是Eason、祖兒、阿詩這些了。)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想要一個有獨特見解的第三者去幫他們演繹出來他們自己的音樂究竟是怎麼樣的。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和這一類歌手合作,因為他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們大部分,除了祖兒之外,都是自己寫歌的,像阿詩、一峰、王菀之,Eason也有,甚至我剛剛開頭做的一些廣州朋友更熟悉的歌手像張敬軒、方大同,都是有很多音樂創作的。

馮翰銘《樂章》
游:那我想跟你說回林一峰的那張唱片《花訣》吧,因為也是拿過華語金曲獎的,你當時也有來拿獎,這個概念是你和他一起想出來的還是說他想了出來再來找你做的呢?
馮:《花訣》是林一峰的概念來的,他來找我和黃馨的時候就說我們能不能一起做出來呢?(游:那個時候黃馨是你的太太了嗎?)哈哈,還沒有,那個時候我們是有交往,我們做什麼都好像一個團隊一樣的,所以一峰就沒辦法二選一,必須兩個都選了的哈哈。我就負責更多幕後監製,黃馨就更多用她的聲音來演繹。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這張《樂章》是有一點點《花訣》在精神上的延續的,是和中國的文化、文字、傳統精髓有關系的。
游:對啊,是和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唐詩宋詞、一種生活的態度又或者是寫意的精神有關的。以前也有關於花的唱片,就像羅文1982年的《卉》,盧巧音也有。但我覺得你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像是在借花講一些關於感情的故事,花只不過是一個象徵而已。
馮:其實那個碟就比較寓花移情,這個“情”是人的情,就像我們的友情,家人的親情等等,我覺得就是中國這五千多年歷史以來的情。我覺得就是一張很人性化的專輯來的,其實我都挺驕傲和慶倖有做過這樣一張專輯的。
游:而且我覺得它的音樂段落編得很好,因為有些部分就是純粹的人聲,沒有樂器的;有些部分就是唱著小調的,所以其實每一個編排都可以看到一個軌跡,一個故事,就像一個音樂劇一樣。
馮:也有少少吧,因為《花訣》在那一年的香港音樂節巡演過的,我們也很想把它帶進內地更多的地方去巡演。我們表面上是說花,但其實裏面包含了很多人與人之間說不出的情的。
游:這句話很有禪意哦,是不是你也會借鑒一些佛教的意識在裏面呢?
馮:其實我很相信世間萬事是有一個平衡點的,就像黑白中間是有一條分開黑白的線,能夠平衡到陰陽,我覺得那一個點就是人生的精髓,而我每一刻都在學習,都在尋找新的平衡點。
游:就是你比較推崇道的觀點——萬物歸一的那種原始狀態。那你也有去研究這些理論嗎?
馮:有看,因為我覺得音樂是生活的一部分,音樂好像我的空氣一樣,但是音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音樂不是全部,它只是我可以用來表達我的資訊的一個工具、一個媒體。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純粹聽音樂而沒有去瞭解音樂背後的故事是會錯失了一些東西的。
游:那除了一峰之外呢,何韻詩的《Reflection》是致敬她師傅梅豔芳的,以前我們都聽過很多致敬的大碟,但這張唱片我們覺得很不同,就是她不是在模仿她師父,是用自己的感情在演繹對師父的那種懷念和一些感受,所以唱每一首歌,是一定和梅豔芳的唱腔不同的,就是何韻詩,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你灌輸給她的?
馮:其實呢,我是今年和阿詩成為好朋友的,因為以往的合作也不是很多。但在剛剛她《共存》這張碟裏,我有試過監製了一首歌,之後發現我們在音樂上,或者說在做人的方面其實很投契。講回《Recollections》,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它和其他的翻唱碟很不同,所有人的翻唱碟,是大家有意無意都會見到一個和金錢有一些掛鉤的像“發燒”、“發燒錄製”、“最靚聲”這些廣告語,但阿詩這張碟是從來沒有標榜這些的,我們都沒有刻意把每一首歌錄製到最高階的音質。因為我們注重的不是最高階的音質,而是最高階的情感。可能我現在和你心靈有個感觸的時候,我們就會立刻錄下來,比如《似是故人來》,其實她很惆悵,不知道怎樣去演繹這首歌,那我有一天和她一起在錄音室裏,就說不如試一下這樣吧,我剛好在琴旁邊,不知道是因為梅姐的提示還是怎麼樣,就是大家會有那一種感受,好像還有一個氣場陪著我們完成這首歌的。我仿佛不知道要怎樣編,但很快我在那個琴上面就已經這樣彈了,那個編曲就已經是差不多大家現在聽到的編曲。整張碟最後那首《夕陽之歌》也是梅姐最後一次公開演出,走上那道天橋然後說再見之前的一首歌,如果大家回想它,其實是非常震撼的。何韻詩的好,我覺得是她沒有刻意去撇除梅豔芳的影子,也沒有刻意去營造“我要何韻詩”,反而是我們兩個去找一個很真實的情感點,認定唱的這一刻、這個當下是我們抱著對師父的一種尊敬的心態和情感去唱,但是要舒服、自然、真心懷念。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因為說那天做事很恍惚或者沒有感受,但又完全熟悉這首歌,就隨便地去唱,我們也從來不會這樣錄,所以整張碟我覺得是有很多情在裏面的。
游:沒錯沒錯,就好像《似是故人來》,這首歌梅豔芳的唱法就比較灑脫,有種仙氣,但是阿詩就是一字一頓,是有血淚的,就是我聽到她用心好像在那裏哭,但是當然她的感情都是有收有放,我覺得那個境界是很難的。就是有種不舍不棄的感覺在
馮:有的,因為其實她真正情感上的是沒有完全放下師傅的。她是很感恩和這麼重情的人,但平時她很男孩子表現的,大家也知道,她也儘量不講這些感性的事情,但我很記得當我編完《夕陽之歌》給她聽了以後,她什麼都沒有說,抱著我哭了很久,因為她感受到那個氣場,有一股愛在那裏。聽起來好像很玄妙、很恐怖,但是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解釋,反正就是很窩心的感覺去完成了這張唱片。
游:是很溫暖,還有一首新歌是《月移花影動》,那首歌也很有意思的,因為找了當年Anita的兩代監製,黎小田和倫永亮,加上你,還有黃偉文,一起完成這首歌,這是一個跨代的合作啊,你們是怎麼組建起來的呢?
馮:他們都是前輩、前前輩!因為這首歌,我和倫永亮先生就惺惺相惜了,他又很愛我的一些編曲風格和鍵琴的觸感,就是一些音樂上的事;同時我又很欣賞他在編曲上很厲害。其實很有意思,我們是沒有怎樣去改他的編曲的,大家現在在碟裏面聽到的編曲,只不過是他用很簡單的工具做出來的東西,我只是再錄了一些真的樂器,去重新演繹他那很細緻的編曲。大家覺得前輩一定是老套,但其實沒有這件事,反而出來的感覺有一些《胭脂扣》之類的影子。對了,《胭脂扣》也是黎小田先生的,但是你又會感受到曆久常新的那種感覺。我這幾年很喜歡做一些可以曆久常新的作品,就像《花訣》裏面的《桂花釀》,這些酒的香醇是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的。我覺得如果要做音樂,都要做這一類經得住時間考驗的。
游:那另外Eason的《The Key》這次也是很不同的,因為沒試過有一張碟可以每一首歌都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而且每一首歌都要從不同的角度去講述戀人或者是朋友之間的關係的,我覺得在香港這麼商業的社會為什麼會有勇氣做這樣的作品呢?
馮:其實《The Key》我參與得比較少,因為那個時候比較忙,但是我反而和作詞的人溝通了很多,其實他有很多很好的關於社會性問題的內容和題材去表達的。陳奕迅是一把很厲害的聲音,任何歌曲,好聽、不好聽經過他的聲音就會變成一首經典的了,他是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歌手的功力。也很高興可以見到香港的詞壇有更多新的人出現,而不是只有(林夕)梁偉文、黃偉文,我覺得是很感激他們的,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粵語歌壇是不會這麼精彩的。他們真的很厲害,而且還保持著這麼厲害。
游:我也覺得近年香港粵語歌的旋律可能沒有八十年代那麼流行,但是歌詞的廣度和深度是比以前大很多的,林夕也有提到這個問題,因為之前有一個李姓的文化家就批評香港現在的歌曲聽不得、不知所謂什麼的,林夕就反駁了這個觀點,我也是非常支持他的,因為那個人根本沒有去瞭解現在的歌詞去到的境界在哪里,但當然這個事情歷史是會說清楚點。
馮:因為其實是很簡單的,現在二三十歲以上的人就會說“那個年代那些才叫歌的嘛!”,是因為他們聽那個年代的歌曲,他是在那裏成長的,甚至有一部分人生就是在那裏的。就像現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等到他們四十多歲的時候他們也會說同樣的話的。所以我覺得嘴巴是長在別人身上,只要做音樂的人真正愛音樂真心想用自己的音樂去發放能量出去感動別人,我覺得已經足夠了的。
游:對啊,活在當下吧!那容祖兒的《小日子》也是很特別的,因為整張碟都用了房間或者說家作為概念,也是改變了她以前一些唱法,就是沒有那麼硬,而是很放鬆,我覺得是最有情趣的一張碟了。
馮:我覺得是她最有女人味的專輯吧。其實和她相處下來我覺得她有一些地方是很吸引男生的,只不過她整天傻大姐一樣,她就不知道也不會去發放那個能量。她的專輯裏有一首叫做《深閨》的歌,裏面的她其實是很懶洋洋的,我覺得是很性感的,不刻意,不暴露,但是就會像你說的那樣,很有情趣。
游:我覺得很欣慰的就是香港樂壇現在銷量雖然是差了,但是在音樂多元化的方面是甚至比八十年代還要豐富的。
馮:對啊,就像我自己是因為受到很重的西方音樂教育的,很多不同地區的音樂人也聚集在這裏,所以就算現在不怎麼賣碟,但是我認為也是百花盛放的。
游: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既然沒有了那麼多巨星,那就意味著你的機會多了。
馮:是啊,既然人人都不賣碟,陳奕迅的唱片都沒人買的話,那大家就不是在為錢做音樂了,真的是為了音樂而做音樂。
游:那說回你自己的這張碟吧,因為之前你一直都是幕後為主的,那為什麼環球也有這個勇氣去為你進行投資呢做一張是由你自己親自唱的唱片呢?
馮:我想因為他們是傻的哈哈。
游:當時我也覺得很意外!因為第一是這張碟的概念很新,全部都用了詩詞的概念,雖然說1983年時鄧麗君也做了一張宋詞的唱片《淡淡幽情》,但是她的方法還是很傳統的,偏中樂的方式去編排,但是你是完全用中國的詞,西方的調式,這個就真的還是打破了常規咯。
馮:對啊,大家比較能接受的是裏面聞一多的《也許》,我和Eason唱的《浣溪沙》這些偏華語的音樂,但是也有後搖滾的《臨江仙》,其實是在紀念葉振棠的《三國演義》。大家還能聽到一些像新的舞曲加上管弦樂的《將進酒》,也有純電影聲的《生年不滿百》,其實就是一張音樂性很豐富的作品。
游:我覺得這是一張試驗品,而且其實可以感受到它是很貪玩的,就真的是在玩音樂的,而不是單純的做音樂。
馮:是的,是真的一張很好玩的音樂作品。但是在好玩之餘,我真的很有使命感去把中國這五千多年來的文化,她的文字的美,去傳達給香港的小朋友去聽,這不是你中學中五去背書這些慘烈的經歷,其實是一段很值得你去尋根的旅程。同時我也想告訴西方的朋友們,中國的文字是真的比你們心中想像的那樣更加美,更加潮,更加有型,而不是只是背詩那麼簡單、那麼俗氣、那麼悶的一件事。如果你真的這麼覺得的話,我勸你,就算翻版,就算非法下載,你也應該去聽一下。
游:我也記得你有一個訪問時有提過這張碟為什麼要做得這麼西式是因為你希望西方的人可以喜歡這些歌,然後再去瞭解中國的文化,這算是你的一個小小的主旨吧。但是不是就因為這樣,所以你特別地把旋律寫的沒那麼好傳唱呢?
馮:其實也不是的,因為在創作每首歌時,我都沒有想太多商業的東西,我只是把當下那首詩觸動到我心靈的感覺直接寫了出來。有時寫完我覺得同一首詩那個氣度、氛圍不合適我,我是會捨棄掉的,其實我已經扔了三十多首,現在只剩下這十一首的了。所以能放在這裏面的歌曲其實是很任性的,就像你說的是在玩音樂。所以我很感謝香港環球唱片,因為他們真的很大風險,如果我把這個概念銷售給任何一個線上的很紅的歌手來唱的話,很可能就是一個月餅盒飛過來了,因為真的很有可能會全軍覆沒的。但是我覺得我做了十二年音樂,我不要只是做音樂來賺錢,我有這個使命感,我需要用音樂、用我的能力去說一些我相信的東西,就是我的根、我的中國文化。
游:那這次你也找到很多巨星一起參與創作,像陳奕迅、陳慧琳、王菀之等等,我想這個過程也很好玩吧?
馮:是的非常好玩,因為在做這個碟之前我已經和他們有很多次的交手了的,所以其實都很熟的了。在真正製作的過程中,其實我是利用了他們的聲音的,因為他們是樂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以歌手的身份來參與的。平時我幫別人做唱片是為了那個歌手,這次我做這個唱片是這一幫歌手為了這些已故的詩人.
游:對,我也覺得他們的人聲是變成了一件樂器一樣。
馮:哈哈,他們絕對是樂器,但是是一件有字的樂器,這其實也很重要,因為主題全部就在這些字上面。
游:正常我們是聽不到這麼冷豔的陳慧琳,因為她相對會更奔放一點點,但那個《再別康橋》真的是很冷、很淒豔,甚至會有孤獨的感覺。這種節奏我很喜歡,只是想不到可以和她的聲音連在一起。其實你是香港人,為什麼這次這張專輯會選擇全部用國語去唱呢?
馮:哈哈這個問題我答了很多次,但是我還是很想繼續回答。剛剛說了,我很想西方的人可以瞭解我們中國詩詞的美,國語來念的話只有四個聲調,而粵語起碼有九聲。或許有的人會批評說像《將進酒》是唐詩來的,你為什麼不用廣東話呢?我也有考慮過這個問題,還去問了林夕,他就說只要你讀的、唱的那個韻腳是押韻的,那麼語言就是通了的,我就讓他一言驚醒夢中人了,因為《將進酒》可能是原著於重慶、四川這些地方的,如果我要追究這些問題的話,那麼我還要考慮這首詩當時可能講的還是重慶話、四川話什麼的,那再說到古漢那些怎麼辦呢?那元曲我不是要找回內蒙的話?所以即然這樣,我覺得就應該用一種現在流通性最強的中國語言——普通話,去讓更多的人來認識我們中國的文化。所以我只是用了這樣的想法,而不是說考慮什麼國語的時常會大一點之類的,其實就是已經沒有考慮這些商業的東西了的,因為我整張碟好像歷險記一樣,有沒有人買對我來說都不重要了,反而是想讓更多人聽到我們華人是有一些國際水準的音樂在這裏的,有待你們發掘吧!
游:可能這張碟不會大賣,但是真的有可能將來會被放在歷史的博物館哈哈,這就是完成你的心願了是嗎?那下一張有沒有可能嘗試回粵語呢?
馮:因為我沒有太大的語言障礙,就算國語不是我的母語,但我算懂;而英語、粵語各一半是我的母語,所以我反而不是最著重那個語言的本身,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情感。我反而會在想,如果下次再做一張唱片,我應該找什麼做題材。其實我也有想過,是不是應該,就像當我去從化或者一些比較偏僻、貧困的一些小村落的時候,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教他們一些小樂器,然後理解他們的風土人情,和他們打成一片,然後回來寫一首歌,或者做一個音樂的概念這樣子。我的下一站,可能去到甘肅,可能去到合肥,也有可能去到雲南……不停地走遍中國,去接觸人和瞭解人與人之間的情,然後將那份情用音樂或者用一張專輯呈現出來,我就是這樣想的,我覺得很好玩。
游:這是一個很大的理想啊!
馮:是啊,我覺得這樣才是一些很真實的音樂,因為我真真正正走進了你的生命,和你一起借著音樂建立一份情。
游:其實都有點像是做一種采風的音樂,或者是一種雲游四海的音樂哈哈。
馮:我暫時想到的就是這樣,希望可以成功實現,因為我真的很想完成這樣的夢想。
游:我覺得可以的,就像我一個朋友也是廣州本地的一個音樂人鄧偉標,在廣州長大,但是籍貫在臺山,他現在就開始在做一些不同方言的音樂,就像他現在在做的一張臺山話的,接下來又可能做一張客家話的,我覺得和你是異曲同工、殊路同歸的,都是想去將一些,本土的、失傳的或者是一些邊緣化的文化用新的方式去傳承,這樣的事可能政府沒機會去顧及到,但如果我們不去做,某些東西可能就失傳了。
馮:是啊,我希望可以繼續推廣文化這件事。像專輯的這張相片其實是和一些已故的先人談著情嘛,我基本上是和死人談著情情愛愛的事哈哈。
游:你覺得如果他們在世,會不會都很認同你這種方式?
馮:希望他們不會被我氣到跳起來哈哈,因為其實我都是很誠懇,很尊敬他們的生平,和他們作詩,那首詩如果有很特別的背景,我都會嘗試去理解,用我現在的一些感受,嘗試去傳譯他們當時的感受,當然曲風會很新穎,希望大家在理念上可以一致。
游:非常期待這張碟會有更多朋友喜歡,除了文化人之外,普通人也有機會去聆聽這張唱片。也希望你的音樂夢想可以成真,希望下次在頒獎的舞臺再見到你!
馮: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