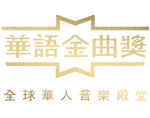華語音樂顛峰對話(三)細聽李麗芬“梳子與刮胡刀”解構樂壇
對話者:華語金曲獎總策劃游威(游)、臺灣資深歌手/廣播人:李麗芬(李)
時間:2013年9月20日下午
地點:廣州南湖頤和大酒店西餐廳
攝影/視頻/錄音:陳小新 文字整理:柯曉婷
鳴謝:蔣明@大象音樂空間


作為臺灣民歌時代唱將、曾以一張哲理警醒的搖滾專輯《梳子與刮胡刀》入選臺灣百佳專輯,並以電視劇主題曲《愛江山更愛美人》成為“國民金曲”的一代紅歌手;以及曾訪問無數知名歌手/音樂人的資深電臺D.J,李麗芬無疑是見證臺灣流行音樂不同年代的傳奇人物。在她淡出樂壇多年後,首次複出擔任第三屆“頤和盛世彼岸花開音樂節”專場表演嘉賓之際,為大家奉獻了一次精彩紛呈的對話,李麗芬以特有的知性、感性。幽默並重,說故事般的優雅語句,“梳子與刮胡刀”的精神,重新解構了她30多年樂壇的如風軌跡。
游:李老師你好,我們這是《華語音樂巔峰對話》,希望邀請華語樂壇的經典歌手、音樂人就音樂未來的發展等方面進行深度對話,之前邀請過很多香港的歌手,而臺灣的您是第一位,很榮幸能夠邀請你!
李:我也很榮幸!
游:李老師,對於我來說您是一位元蠻資深的前輩音樂人,因為在很早的時候就買到您的卡帶,那個時候我們主要還是聽卡帶的。您的第一張唱片(合輯,與吳楚楚、潘越雲)《三人展》是在81年的時候就出了,現在在收藏市場價值很高啊,因為到後來九十年代才普及CD嘛,很少人有這張黑膠,我到現在都還沒找到,但是我有收藏你86年那張《梳子與刮胡刀》,太經典了。我們談談那張專輯吧,因為它太重要了,也是很多人認識您的一個開始。當時1986年是民歌到都市流行歌的一個轉折期,也包括一些搖滾歌曲什麼的,所以臺灣歌曲的風格就開始跟民歌時代那種清新、人文、雋永的氣息有所不同了,更多了一些控訴和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我覺得您的這張專輯也特別能夠反映這一點。專輯的第一首歌《城市英雄》,這首歌也是非常經典,我覺得它的角度非常新穎,因為它所講的英雄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種很偉大的英雄,而是平民,或許你覺得他們的生活可能就只是上班下班,但我們的城市就是由千千萬萬這樣的普通人構成的,所以我很想瞭解當時是怎麼構思到這首歌的呢?
李:因為當初這張專輯的出版和發行是同一個人——吳正德,也就是說他是有帶著理想去進行這張專輯的,幾乎所有的構思和概念都是由他一直醞釀並且希望在商業市場上的作品裡傳遞的:情歌太多太膩了,也貧乏了,但是如果做呐喊式搖滾,可能有些人會反抗或者抗拒,所以他在聽我唱歌的時候,就清楚知道他需要的是一個冷靜的聲音,不能太女性化,但是也不能是一個男性。我在《三人展》之後是拿吉他唱的,後來遇到了瓶頸期,那個時候新的美國音樂形態開始進入中國,所以我也就放下木吉他開始了和大樂隊的合作。吳正德當時聽了之後也覺得非常合適,所以就提出要做一張完全概念化,傳遞理念和思想的唱片,而不是一般普通的流行作品,我也喜歡做一些特別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很不錯。在我們前期的準備到後來的選歌、錄音都是特別用心的,特別是在詞的部分,他是希望跟一個固定的詩人合作。你看到的是歌詞,但是是介乎在詞和詩之間,一般人也可以看得懂聽得懂而且還可以傳達理念思想的作品,這在臺灣流行樂壇上是第一張完全由詩人來寫詞的專輯。(游:就是童大龍老師?)對,就是童大龍,也就是夏宇(臺灣著名女作家,本名黃慶綺,也用筆名李格弟)。我在跟她碰面的時候非常驚訝,因為她的個兒非常嬌小,但她非常有思想,就是用思想在表達自己。那對她來說也是一個考驗,因為寫詩對她來說簡單,就是抒發自己的心情,但是如何讓詩的那種大意境由深入淺,深入人心,就是一個挑戰。吳正德這個製作人很重要,在理念上他想傳達平民社會裡,社會中下階層這個金字塔下面最穩固、最需要他們的這樣一個階層的生活百態,還有一些生命上的一些感想。
游:對,因為我覺得臺灣之前的專輯更多反映的是一些知識份子的心聲還有理想,更風花雪月、更靠近傳統詩詞歌賦一點,但是這麼寫實、這麼底層、這麼市井就真的很少見,我們可以看到專輯另一首歌《越挫越勇-上等兵》,這首反映臺灣老兵退伍之後生活的歌曲,我記得當時還有其他一些電影,像《搭錯車》也是反映這樣類似的題材,但是這首歌寫得挺悲情的,還有對他們的一種關照和憐憫。
李:對,因為臺灣有兵役的制度,每一個男生,除非你是有問題,大部分都要服兵役。那這個東西會讓一些年輕人把剛好可以發展事業的機會在兩三年就耗掉了,在他們服完兵役回來和社會接軌的時候是會有困難的,很多人當完兵回來也就是二十出頭,這個時候他們就需要開始打拼了,很多人也會選擇去當業務員。
游:對啊,我就看到歌中說老兵開著摩托車去推銷……
李:是啊,它說的就是時下年輕人都需要服完兵役之後,重新開始打拼還要一邊適應社會。我雖然沒有服兵役,但是我自己也是很小就獨立,打工自給自足,很早就開始打拼,當你在打拼的時候會發現有很多跟社會不適應的地方,然後錢又少,我記得以前去吃自助餐,那個時候在臺灣有這種專門給平民百姓的自助餐,大概就是五十塊台幣,可能是十塊人民幣,就可以買到一個便當,已經算蠻豐盛的了,那你就沒有多餘的能力去吃其他的東西了。所以說克勤克儉是那個時代的一個背景。其實我們那個年代沒有像現在這麼富裕,我們要什麼東西,爸爸媽媽不太可能可以供給給我們,所以那個歌,當初她詞寫出來之後,她認為曲是可以輕鬆一點的,那個調性不悲,我和夏宇都是女孩子,但是到了作曲人是男性,所以那種感觸就激發了他所有的思緒還有情緒,融入在了曲子裡頭,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對於任何人都是這樣的,在打拼的時候,“把理想交給遠方,把風箏還給童年”,在成年長大後,怎麼都切斷了,但是還帶著一絲夢幻、浪漫,還有善良,認為這個社會是美善的。這首歌在前奏部分用到了一些戰爭的聲音,(游:對啊,那個很經典!)那是因為在那個時候,任何時間裡頭,我們都會有一種緊張的狀態,認為有可能要打仗,所以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危機意識。這首歌是感動了很多人的,因為男生們都有感觸,服完兵役回來女朋友跑了,自己又要從零開始,兄弟的情誼進入社會後,對不起,因為社會是現實的,我們都學會了鞠躬哈腰……臺灣服完兵役之後是沒有像大陸那種分配制度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從零開始。其實回想到以前,高中畢業後有個男朋友,他去當兵時,頭髮一下剪得非常平,背著一個背包,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衣服,我還記得當時陪著他的家人,看著他走上火車,他帶著有點迷茫的眼神看著我,我也不知道未來是什麼,然後就這樣看著他離開。他離開後一年過去了,他又外島去,我們就頂多靠信件聯絡了。那個時候我在民歌餐廳唱歌,就碰到一個粉絲是德國人,他對我非常非常地忠實,一直來聽歌,也非常欣賞這些歌曲,還跟我學吉他,慢慢地就會有一些親密的情愫,我就再交了這麼一個男朋友,所以就作為一個女性在聽《上等兵》這首歌時,其實都是百感交集的。
游:所以其實也有投射你個人的情緒在裡面的?
李:對,一定會有這樣的,因為這是人生的一種經歷,都是點點滴滴的。我們在那個時期開始做音樂的時候,製作人就非常明確的,歌曲一定要和歌手本身的個性、經歷背景以及生活內容有結合,才不會脫節。我們的目的是說歌手在唱一首歌的時候,會讓人覺得那是他的作品,做到這麼融合貼近的時候才是最成功了。所以當時製作人也有和我聊我的生活狀態等等的東西,他就一直覺得我是一個非常冷的女子,那因為我的冷是來自于小時候爸爸媽媽,他們當時是拼盡力氣,生到我的時候已經是覺得“啊,完了,又是一個女生!”重男輕女嘛,所以後來就不太跟我有互動。家庭就是小社會,從小我都有點像旁觀者,看父母怎麼跟家裡其他小孩子互動的,所以就養成自己這種比較冷的旁觀者的個性,後來進入社會我也沒有很學習到如何去跟別人親密互動,也鬧了很多笑話。所以後來他們也形容我是“薔薇女子”,就是專輯裡那首歌。後來我覺得也是如此的,以為你在聽我唱情歌的時候,會發現我沒有什麼大的情緒起伏的。
游:你是天蠍座嗎?
李: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天蠍座,但其實我是巨蟹座。我很柔,而且非常感性,感性到當時在做《城市英雄》的時候,突然所有記憶就片片斷斷地湧現出來,情緒就濃了,就掉淚了。我記得那個時候,錄音師就讓其他人先出去,讓我一個人稍稍冷靜一下。我常常在唱歌的過程中也會這樣,就是太感人的時候也會掉眼淚,那我就必須在冷靜下來再唱。
游: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寫實的作品以外,另外一首就是《梳子與刮胡刀》,它是包含一種蠻有哲理性的比喻,這種比喻我覺得在華語樂壇好像都比較罕見的,居然可以用這麼平常的一些生活物件去表達對於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的心情,真的很精簡,不知道怎麼會寫出這麼好的歌詞?
李:哈哈,希望有機會可以讓夏宇自己來聊聊她的想法!我知道她在早期的時候是接觸舞臺劇相關的工作人員這樣的藝術人士,他們在觀察人生百態時的角度是比較不同的。後來等我過幾年再去唱這首歌的時候,我覺得它講的就是中國人的道家思想,生生不息,然後回到原點。一般人看這個歌詞的時候,可能會覺得為什麼不甜一點呢?或者為什麼不震撼一點呢?但是我是很冷靜的,那個時候我沒有任何其他的猶豫,我覺得這就對了,所以最後呈現出來很輕而易舉地就可以達到一種獨樹一格的效果,不敢說是最棒的,但要傳達的東西是傳達出去了。
游:那有一個疑問就是,為什麼第一張《三人展》是滾石唱片公司出的,後來又變成喜馬拉雅出了的呢?沒有簽約滾石嗎?
李:哈哈這個非常有意思,因為滾石剛開始在創業的時候是做雜誌的,他們在嘗試如何能做成唱片公司,所以是需要一些機會,而在出了《三人展》之後,也是收到訊息是我們可以開始做個人專輯了的。當初吳正德也是在滾石從基本的製作助理做起的,我知道他的想法的,他想做一些冷靜的東西,因為那更有力量,但是發現在滾石沒辦法實現這個夢想,所以只好離開滾石了,最後就選擇了喜馬拉雅來發行。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需要製作人對理念始終的堅持,我們沒錢,所以錄音需要和音的時候,只好自己來,包括製作人吳正德,所以你聽到《真心英雄》裡面有一段出了我的聲音之外,是老闆員工全動員的,哈哈……我們那時沒有錢去宣傳,上不了頭條,也上不了版面,正好劉文正先生聽了那張專輯,他非常欣賞,主動打了電話聯絡媒體,還幫我們請媒體吃飯,所以我真的蠻感謝他的,這是我頭一次感到在這個現實的圈子裡快要無力了的時候,有人來幫助我們了。後來幾年吳正德自殺了,這是真的非常非常遺憾的。
游:你會不會感覺像失去了半個支柱,因為他在音樂上是對你最理解也是最支持的一個人……
李:其實我在跟吳正德合作的時候有感覺到一點他的那種執著到固執,甚至有一點偏激的這種藝術家深度的個性,那梵古也是這種個性的,到最後受不了了,我可以理解。對於這麼一個藝術家來說,我不妥協,但是我又沒有這麼一個強大的經濟能力,理想實現了,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平衡,在財務上頭可能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在這種狀態下他還要繼續經營下去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可以理解。可能就是這樣種種的壓力之下讓他鑽進了一個牛角尖,但其實我認為他已經是完滿的了,在道家思想上講,生命是輪回的,至少他不用那麼痛苦了,這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太痛苦了,所以當我知道他離開的那個時候,當然我心裡頭會有遺憾不舍,但是其實私心更深處的地方是覺得,終於他可以解脫了。
游:在你後來去做廣播節目的時候,會不會有一個角色的轉換,因為以前你是藝人。都是別人來訪問你,或者說你是一個跟著自己的想法走的人,但是去做媒體的時候,你需要在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去觀看藝人的內心,這個會不會有一個抽離的過程,也跟你以前的生活有一個反差,心裡會不會有一個轉換,一會兒是音樂人,一會兒又是廣播人了?
李:還好,因為我是一個腦袋比較簡單的人,在做事情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分心太多,所以在做這個的時候我就不會做那個,正好那時候唱片的宣傳告一段落,我也可以全心投入廣播去學習,去經歷。其實我做的是音樂節目,還是可以播音樂、介紹音樂啊,而且長期以來包括自己演唱都會涵蓋民歌、西洋的民謠、西洋的流行歌曲、爵士、布魯斯、搖滾、鄉村等等,我已經聽了一大堆,所以居然就變成我非常豐富的資料庫。然後無論在介紹歌曲還是訪問歌手的時候,我都可以有一個很扎實的基礎去吸收、整理、消化,所以很快我就可以駕輕就熟。
游:到了九十年代重回滾石,小蟲幫你製作專輯(《發現》和《就這樣約定》),把你的聲音從很冷變得溫暖,或者說更面向大眾了,包括中國風,還成為電視的主題曲,這種轉變當時你們是怎麼溝通的呢?還是你自己也有心理上的轉換?
李:我跟小蟲合作的時候不怎麼談私人的經驗,他也不會問我私生活方面的東西,其實我覺得他通過廣播對我已經有一點點瞭解,另外是我很信任他,我覺得他非常專業,可以市場化但是又非常地有內涵,所以我都不會過問太多,都是他大概整理好了一首歌一首歌的小樣到我手上,我一聽,以我自己的經驗來判斷,就知道是不是適合唱,會不會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但都沒有。但那些都是小樣,沒有變曲目,所以我拿到編曲一看,哇,那麼東方,我覺得是瞠目結舌的一個狀態,但後來想想覺得也沒什麼好抗拒的嘛,而且唱一唱也覺得,蠻搭的嘛!進錄音室的時候,小蟲也有意識到這是比較大的差異,但他就跟我說,你不要想,不要去思考,就唱,根據編曲的感覺就去唱,我剛開始會有一點卡住,但排除干擾後專心聽音樂越進越深,因為從小長大也會受爸爸媽媽影響嘛,他們聽什麼音樂你會耳濡目染,那我爸爸會聽舊上海時期白光、吳鶯鶯等等之類的歌,我媽媽就會聽地方戲曲,這些東方的音樂是在我的基因裡的,所以唱著唱著很快很快就感覺自己改變了,甚至自己都有點不習慣,確實自己去聽的時候會覺得,哇,這麼地不一樣!(游:很豪邁?)對對對,《得意的笑》還不夠豪邁呢,我覺得《愛江山更愛美人》就真的很豪邁,那種豪邁和冷靜是你自己在唱的時候都完全沒有察覺的,因為我覺得小蟲在透過廣播瞭解我後會發現我講義會比講情多的,所以在後面的製作當中,他都可以捕捉得恰到好處。我不是一個濫情的人,所以在唱的時候會處理得稍微冷靜一點,如果換成一個男聲來唱,馬上就會變得大海磅礴那種,但是如果其他女聲來唱可能就會變得很淒涼很嗲的了。而《月兒彎彎》是另一個部分了,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柔軟很容易掉淚的人,也很容易有同情心的人,不忍拒絕別人,不忍看別人受苦,那這些也是會透過聲音去表達的,小蟲瞭解了,我們兩個合作就很像朋友,沒有什麼太嚴肅的製作人、歌手的身份界限,就是音樂愛好者,我懂他,他似乎也懂我。當我拿到《月兒彎彎》的樣本的時候,大概聽一下就覺得很不錯,小蟲和我都是很隨性的,在還沒有正式錄音之前有一天,他正好坐在鋼琴前,就很即興地彈奏了《月兒彎彎》,我也很投入,所以後來進錄音室的時候就很順利,我跟他的合作做這個出版品可以說是最快樂的一個過程,那時也是唱片工業的巔峰時期,所以大家合作都很開心很窩心,我現在還很懷念那段過程,包括一起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員。
游:那我最後想說,如果在內地香港臺灣挑一個音樂人或者歌手,你最欣賞或者你合作得最好的、最想跟他合作的,你會挑誰?
李:我覺得我挺欣賞汪峰的音樂態度的,十年前在臺灣我收到他的第一張專輯的時候就採訪了他,而且是我主動打的預約電話,其實那張專輯很小眾沒有多少人留意到的。當時我電話訪問他,他在走穴,沒有車子,沒有房子,什麼都沒有,很苦的,我記得當時特別有跟他說一句話說你的音樂作品很棒,我聽了很多次了,你會有非常棒的自由的,果不出其然,這麼多年之後已經很紅了,然後他近期的作品也可能會比較貼近市場了,但是我認為至少沒有失格。一個藝術家在貼近市場的時候很容易失格的,但是他沒有,那個部分還在,所以我還是很欣賞他。
游:我覺得他現在的歌跟李宗盛那種比較像,就是貼近都市,宣洩中年男人內心一些呐喊的情緒,但是他通過他一種比較白描的處理,就沒有以前那麼憤怒,可能這種態度這種宣洩正是他需要的。
李: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合理的,你不能讓一個人從二十歲搖滾到五十歲嘛,搖滾是一個精神,但內容和情景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那說到臺灣的話,我最敬佩的一個音樂人是李宗盛。有過一次機會可以和他合作的,但是可能是時機未到吧,另外一點,我覺得他可能會和歌手磨,磨很多次,把作品做得很精緻,而且他是會重新打造歌手的,那我又是一個很冷的人,可能會有一些地方讓我有不安全感,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了,那時候他也還沒紅,我也繼續在唱我的這些西洋歌曲。李宗盛在臺灣流行音樂史上我覺得是一個比羅大佑還有影響力的人,因為他除了是一個製作人、詞曲唱作人之外他還懂得如何讓一個歌手用新的歌曲和唱腔去傳達自己,而不是通過包裝企劃的東西,他會賦予歌曲生命,而那種生命是富有思想的。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也一樣,用自己生命中的經歷,非常接近社會底層,從不媚俗。他自己再去重新詮釋這些歌手演唱過的歌曲時,我覺得是超越了的。他的唱歌的方式,幾乎像是在傳達思想的方法,像說話,但又接近唱歌的旋律,這個力量是非常大的,像是很想把自己的生命擠壓了說出來那樣,這就是藝術家,你看到他的作品是沒有話說的,而且就算在批判一些事情的時候,他是比羅大佑來得更幽默的,有種天天笑看人生,但是自己又在紅塵打滾的狀態。他也常常會說,與其去修理別人,不如先修理自己。可以說,李宗盛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對臺灣流行音樂史是建立了一個做音樂出版品的模式的,這個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是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做他的作品的。
在香港這方面來說,我認為就是梅豔芳了,你給她什麼歌她都能唱,她也是一個很冷的歌手,(游:跟你當年那種冷是不同的吧?)我比她多情我覺得,她更冷。(游:但她其實有種悲情吧?)我覺得可能也是她個性的特質吧,另外我覺得她是在娛樂圈裡比較難得的一個講情義的人,可以表裡都一套很有影響力的,這很難得。你在她的音樂出版品可以聽到她的聲音有瑕疵,但是她都不掩飾地表達出來的。包括她舞臺上百變的模式,都是無人超越的,她的天賦,也是激發了其他藝人原來可以這樣包裝等等之類的,我覺得,這就是梅豔芳。
游:那最後想和你探討一個問題,就是近年來選秀,特別是內地非常火熱,像《中國好聲音》之類的已經改變了唱片產業的模式,從唱片製作模式變成選秀模式,因為傳統的那種唱片製作、包裝,很難再產生這樣全國風靡的藝人了,真的只能在選秀裡還能看到這樣的奇跡,你是怎麼去看待這樣一個產業的轉型的?
李: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因為音樂出版品的部分,如果沒有酬勞,就肯定會停止,CD賣不出去或者賣得很少,大家就不敢做了。再說到音樂下載是要付費的,現在還不成氣侯,但是將來是一定會實現的,那在這個過渡時期就正好出現了這些東西。去做了那麼多次的評委,我也感覺到在音樂這個方面希望嶄露頭角的歌手是很多的,我覺得有一點是很可惜的,因為這種節目很難做,要怎麼去包裝一個歌手讓大家覺得他是誠懇的,這是很困難的,因為大眾不是愚蠢的,而且讓人印象深刻的永遠都是細節。但其實我覺得這些選秀節目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都包裝得太高亢了,真正感人的沒有多少。這是小小的遺憾,但我相信以後會改變的!